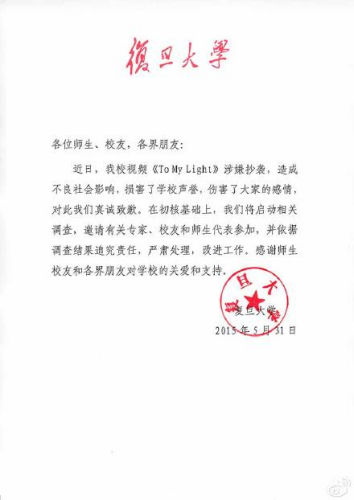近日,有媒体报道,宁波浙江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女员工在面试时告诉公司自己近期只能短期内不打算结婚,然而该女子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孕期几乎没有正常工作,休完产假之后随即提出辞职。在这名女员工怀孕期间照常给她 ...
近日,有媒体报道,宁波浙江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女员工在面试时告诉公司自己近期只能短期内不打算结婚,然而该女子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孕期几乎没有正常工作,休完产假之后随即提出辞职。在这名女员工怀孕期间照常给她发工资、交社保的公司表示很无奈。
此事一经报道,便引起了诸多众多争议,。有人认为该女员工的做法是“碰瓷”公司,凭借公司无法孕期辞退自己,来“蹭”孕期待遇;但也有人认为,女性在求职市场中本身就是弱势,“隐孕”不过是为了对抗企业的用人偏好的不得已的选择。
对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就女员工“隐孕求职”是否涉及法律问题,以及求职过程中法律对女员工和公司两方权益的规定与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隐孕”并不违法 唯一可能是涉及诚信问题
“隐孕入职”,指的是一部分怀孕女性,隐瞒怀孕入职。从法律的层面讲,这是一部分怀孕女性在寻求合法庇护。《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明确:“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所以,“隐孕入职”本身并不违法。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副教授娄宇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除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附录中列出的女职工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之外,其他工作都是适合怀孕女职工的。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李亚娟也认为认为,劳动者有一个签订合同时的如实告知义务,但范围限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如果岗位是孕期禁忌或限制岗位,则应如实告知,以免影响孕妇及胎儿健康。而如果岗位不属于孕期禁忌或限制岗位,则劳动者不需要就此告知用人单位。”李亚娟解释道。
两位专家都强调,我国现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都就女性劳动者孕期、产期、哺乳期进行了规定,以保护孕妇及胎儿或婴儿的利益。
李亚娟将其中涉及到的具体的保护归纳为了六个方面,分别是:女性“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不得解雇、孕期工作调整、产假保护、生育津贴、哺乳期保护、孕产哺乳期设施建设。
“入职后怀孕没有任何法律问题与障碍,女员工隐瞒自己怀孕情况入职唯一涉及的可能是诚信问题,女员工则利用了现有法律对孕产哺乳期女性的特殊保护,但现有法律却没有相关规定对该类行为进行限制,便会对企业利益造成损害。”李亚娟说道。
娄宇副教授还表示认为,相关法律并未对“入职后怀孕”与“隐孕入职”进行具体区分,因此,一般情况下,并不存在“隐孕入职”一说,因为无论女职工是否隐瞒,单位均不能因为怀孕就不录用。
““如果单位在入职体检中发现女职工怀孕,一般也不能取消录用,因为入职体检往往是录用的最后一步,取消录用意味着单位基于怀孕事实实施性别歧视,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娄宇副教授补充道。
“隐孕”或侧面反映就业性别歧视 企业无权制定限制性条款
关于“女员工产假结束就辞职”一事引起的广泛关注,李亚娟副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此事曝光后,企业从用工成本的角度出发更缺乏雇佣女性劳动者的愿望与动机,整体女性的利益也会被损害。
李亚娟副教授还认为,除极端个例事件外,部分女性隐瞒自己怀孕情况的背后,反映的仍是就业性别歧视的问题。“李亚娟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生理、社会和家庭的平衡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在目前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女性可能将会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这无疑更加重企业的顾虑。”
娄宇副教授则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这不具有普遍性,仅仅是劳动关系领域的一个个例。”
他进一步解释道,“单位录用劳动者除了性别的考虑之外,还有对劳动者技能、学历、工作经历等等很多因素的考虑,女性职工也有对自身职业发展前途的考虑。任何单位都不会将育龄劳动者天然地视为‘隐孕入职者’,虽然这件事可能会对整个职业女性群体的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是这种损害微乎其微。”
就业性别歧视的情况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女性生育成本大多由企业承担,因此企业会在招聘对女性求职者充满顾虑,或对女性员工做出“几年内不得怀孕”等限制性要求。如实告知怀孕情况或怀孕计划便可能失去被录用机会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怀孕这种生理状况导致女性丢掉工作或者不具备求职资格,女性应该沉默吗?
“企业禁孕条款与禁婚条款都是违法的。”李亚娟强调道。
娄宇副教授对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可能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情况给出了建议。“在招聘和录用阶段,由于女性求职者还不具有劳动者资格,只能申请调解或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一般按照缔约过失或者侵权来处理。而在劳动合同的履行阶段,可以通过调解、仲裁和诉讼来维权,仲裁是诉讼的必要前置程序,一般按照劳动纠纷来处理。”
生育成本社会化强化政府责任与男性义务
对于有网友人提出可以出台黑名单等诚信管理制度来约束“‘碰瓷’企业”现象发生的观点,娄宇认为劳动者黑名单制度很难起到期待的效果。
“一方面,用人单位很难证明劳动者有‘隐孕’骗福利的故意,即使在入职体检时或者入职不久后被查出怀孕,也不能想当然认为劳动者在欺骗用人单位;另一方面,建立诚信管理制度需要成本,如何确定诚信的标准,谁有决定权将劳动者放在这个名单之中以及如何处理诚信档案和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论证。”娄宇解释道。
而为避免企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李亚娟副教授则认为可以考虑在就业招聘中推行就业推荐信制度。“初次求职者可以提供学校老师、社团组织负责人、社会实践负责人推荐信,再次求职者可以提供前一次用人单位推荐信。”
她同时李亚娟副教授还指出,在生育成本社会化过程中,如果仅由企业来分担生育成本的话,企业从利润出发会拒绝招聘女性求职者,因此生育成本社会化应该强化政府责任与男性义务。“强化男性家庭责任也是一种方式,比如强制性育儿假延长男性育儿假等。”
对于另一观点提出的通过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的倾斜,如税收优惠等方式,来降低企业的负担的建议,娄宇副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依据税收法定原则,设置税收优惠的立法成本和监管成本同样不低。并且并非所有女性职工都会怀孕和生育,企业很难评估女性就业对劳动效率的影响。”
对此,娄宇副教授提到了德国的男性产假制度。“以家庭为单位,男性职工也可以享有不低于女性职工的产假,可合并实施之前的生育保险,相关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负担。”
“这一做法在实质上也贯彻了“社会事务社会治理”的原则,雇佣男性和女性付出的生育成本是一样的,便可消除企业的顾虑,”娄宇副教授补充道,“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性别差异在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即男性也有义务关照家务,女性也有权开展职业生活,让人得到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