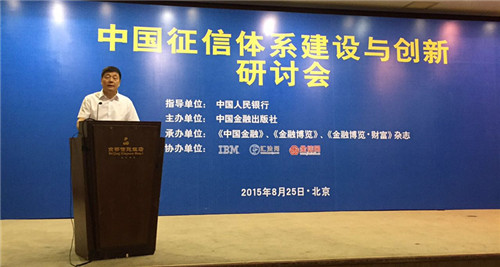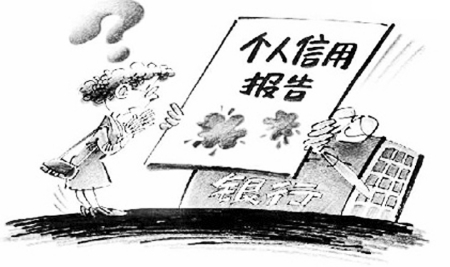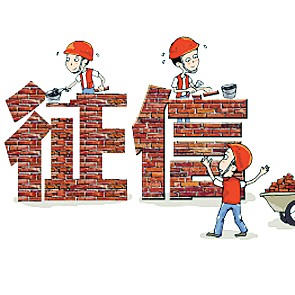新华网6月19日刊发一组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让江苏睢宁县再次陷入舆论质疑风潮。该县4年前推出大众信用评级制度时,已被讥为“在发放良民证”。两次质疑的焦点完全一致:政府征信会导致公权侵犯私权。(7月2日《 ...
新华网6月19日刊发一组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让江苏睢宁县再次陷入舆论质疑风潮。该县4年前推出大众信用评级制度时,已被讥为“在发放良民证”。两次质疑的焦点完全一致:政府征信会导致公权侵犯私权。(7月2日《新京报》)
俗话说,人无信不立。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这是越来越清晰的共识。《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2003-2013)》显示,截止2012年我国征信机构达到140家左右,总规模达20亿。此外,国务院近日还专门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推动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征信建设既迫在眉睫,又是大势所趋。于此而言,4年前的江苏睢宁就在大众信用评级实践上先行先试,且不论其走了多少弯路与歧途,起码初衷良善,勇气可嘉。
客观地说,眼下少数媒体所谓“良民证”的诟病,确实是不负责任地炒冷饭。2010年9月4日,睢宁出台全国首个《个人信用管理试行办法》,脑残规定一石千浪。不过,2011年1月,新修订的《办法》出炉,早就取消了相应的4个诚信级别,即“诚信、较诚信、诚信警示和不诚信”;如发生失信行为,只如实记录类别和分数,不再对个人诚信定性。更关键的是,引起或易引起社会争议的20多个条款和评分悉数取消,其中就包含目前网上热炒的所有内容。
当然,睢宁的信用实践备受质疑,核心无非是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主导的信用建设,会否因为立场与技术因素,而沦为掣肘民众权益的信用游戏?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杞人之忧。拿最早的版本来说,譬如对于“获得信用加分可优先低保评选”,常识上说,低保是针对贫困人群的,信用加分跟贫困有何关系?又譬如由于将闹访等行为纳入信用评级,新政一出,便坐实为行政部门懒政思维下“合法伤害权”的显性化。即使是修订后的版本,更多细节,也存在不小的瑕疵:一是睢宁县称,征信办设置了征信通知个人的环节,但实际操作中,对被加减分的个人,“未全部通知”。二是据说2011年出台了修订本,但“怕公开后引起新一轮炒作,所以只在内部运行,没对社会发布。”若是好好的征信系统,非要偷偷摸摸地进行,程序正义上先就打了大折扣。
那么,谁来征信、谁能征信?
睢宁县的这套“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自2010年1月1日推行,是当地政府花了80万元开发的征信系统,征集本地14岁以上114万居民的个人信用信息。据说,此后睢宁“已由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管理县变成先进县,由金融高风险区域变成全国金融生态示范县”。我们自然无法从结果来倒推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像当地一名政府人士感叹的,“睢宁的政府版征信,在原点就有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悖逆专业服务市场化的历史大势。2013年3月15日,我国第一部征信行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譬如根据《条例》,央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事实上,目前信用评级公司、主业为金融信息化的上市公司、P2P平台、第三方支付公司、民间金融服务商等各路资本都在争相抢滩征信业。在人口流动性加强、大数据来临的今天,地方“圈地”征信建设,恐怕容易吃力不讨好;二是立场与利益难以撇清,容易做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市场经济下,地方政府本身就是需要接受信用评估的主体。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信用评级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重点从经济运行、财政收支、债务等方面评价分析地方的信用状况。事实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早在密切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也曾有机构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作过评级。这个时候,让客观公正的征信工作落入地方政府囊中,难免令人怀疑这是否是一种角色上的错位。
征信虽好,也非万能。在信用发达的国家,也不会事无巨细都甩出扣分的棒子吓唬人。中国信用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厘清主体、遵循规律,方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